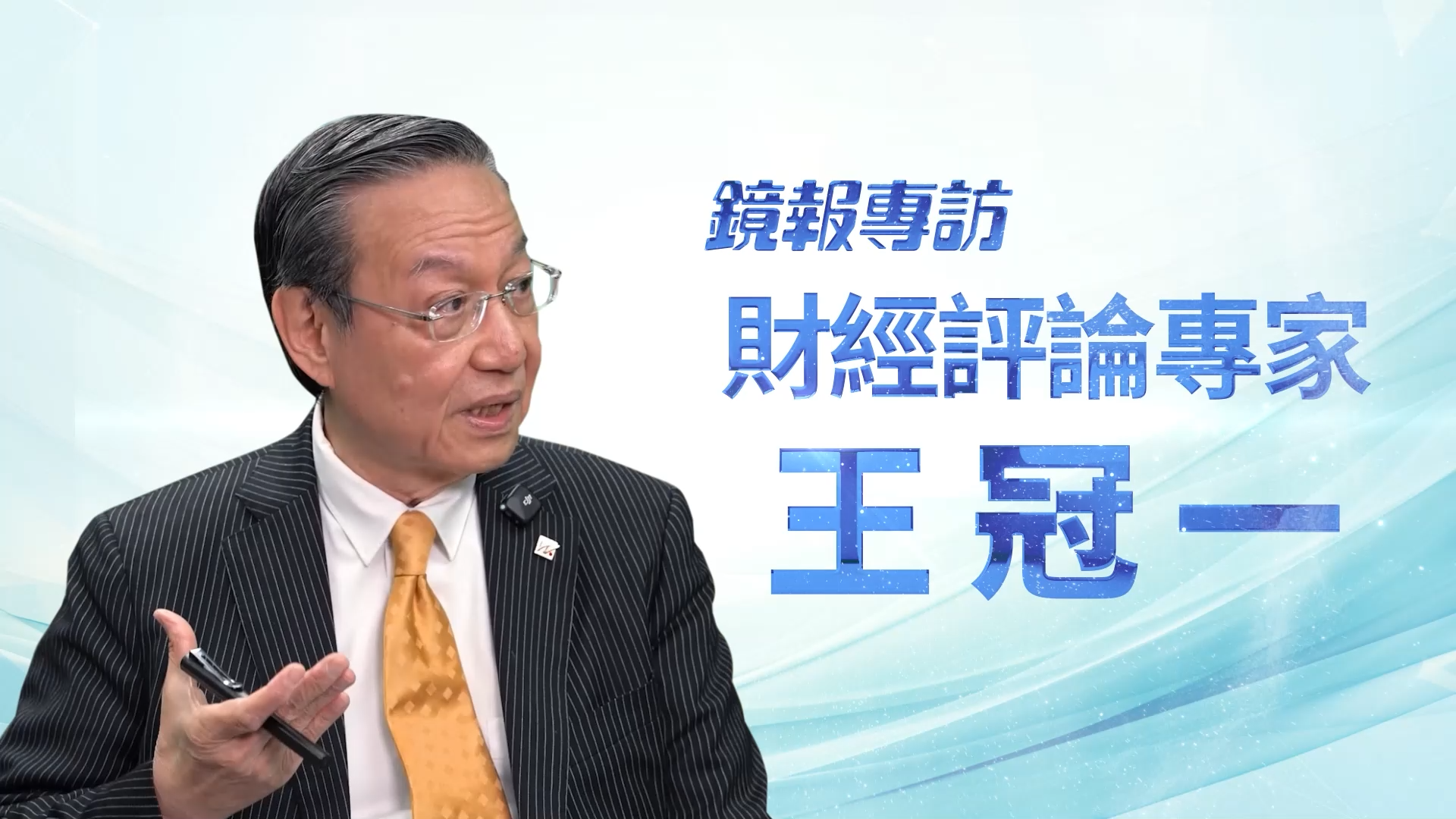從繡線到史線:徐婉玲的非典型學術之路
發布日期:2025-06-10 林青「你來啦!」北京故宮博物院檔案館副館長徐婉玲熱情地招呼着筆者踏入她的工作地——位於博物院西南角的寶蘊樓,這是一座擁有近110年歷史的二層馬蹄形小洋樓,樓前兩株海棠花正絢爛綻放。
這位知名的故宮史學者毫不避諱自己出身於農村。「我是浙江台州人,父親務農,母親以刺繡為生。」家中無人設想過這個農家女孩能讀完高中,更遑論大學。她曲折的成長軌跡,是內地「70後」女性的一個縮影:她們是內地改革開放的同齡人,她們走出家門、走進課堂,她們的職業選擇受時代機遇牽引。
25歲前從未踏足北京、更不曾親眼見過故宮一磚一瓦的浙南女孩,卻能在北京故宮「擇一事,終一生」,徐婉玲說,這是非常奇妙的人生旅行。
縫紉機還是講台
1980年代的浙江台州農村,空氣裡彌漫着學縫紉的熱潮。11歲的徐婉玲,在母親幫助下,用縫紉機繡出一隻憨態可掬的熊貓。這幅以「國寶」命名的機繡作品,在小學生手工比賽中得了獎。一項謀生的技能,在她的手裡成為一件小小的工藝品。「這是我小時候印象最深的事情。」
按當時江浙地區的傳統,女孩很小就會回歸家庭作坊做學徒,刺繡就曾是徐母賴以生存的手藝。由於學習優異,在老師的推動和母親的支持下,最終,徐婉玲得償所願,懷着一腔文學夢,叩開了浙江師範大學的大門。只是,因為選擇服從專業分配,填報了旅遊管理與服務教育專業的她,最終與漢語言文學專業失之交臂。「成長中,你常常會發現,有很多最初既定的目標,會因為一些未知的選擇而發生改變。」
大學畢業,徐婉玲堅決不考研究生,「那時的我一心想要工作」。2001年的暑假,她順利獲得台州學院的教職。這是一個鐵飯碗,父母都很高興。不過,她在給學生們講課時,學旅遊管理的人,第一站總會想到北京,北京的第一站一定是故宮。太和殿的斗拱、飛簷上的神獸——這些給學生們講過無數次的課文,總得親眼看看呀!徐婉玲那時在心裡埋下一顆種子:「有一天,我要帶着相機,站在故宮的紅牆下。」
「北漂」者的學術啟蒙
25歲那年,徐婉玲放棄了台州學院的編制,成為一名「北漂」。讓她走出家鄉的是一份北京大學旅遊研究與規劃中心主任助理的工作,「辦公室就在北大校園內」。在最初的日子裡,由於SARS疫情的肆虐,她經歷了人生最迷茫的時期。工作能按部就班地完成,但孤獨令她無助。為了化解糟糕的北漂初體驗,北大著名的信息集中地「三角地」給了她新方向。很快地,她在北大西門外的蔚秀園找到了寄居的地方。一套50多平方米的小兩居裡,住着六個女生。在這老破小的空間裡,只有一張小小的床鋪是自己的,有些擁擠,但卻充實,因為這些來自天南地北的考研學子激勵着她認真思考着自己的未來。
在同伴們的介紹下,徐婉玲報名參加新東方英語培訓,旁聽北大歷史地理課程,開始着手考研。「We will hew out of the mountain of despair a stone of hope(從絕望之山劈出希望之石)。20年多前在新東方學的這句話直到今天還記得。」徐婉玲回憶,「那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群體,各種各樣的朋友互相分享知識和信息。那種氛圍,讓人很難不想繼續讀書。」
徐婉玲說,「人生總會經歷一些起起伏伏。」2005年,她度過了一個最揪心、最糾結的暑假。那年,她報考北大歷史地理專業,雖然研究生考試總分排在第二名,但英語單科成績離錄取線差4分,未能如願考取北大。最終,她調劑到中央民族大學,就讀考古學與博物館學專業。
幸運的是,她在中央民大遇到了自己的學術啟蒙人。彼時,從事吐魯番學研究的張銘心博士剛剛從日本留學回國。作為他的第一名碩士生,徐婉玲得到了嚴格的學術基礎訓練,也獲得了珍貴的學術調研機會。
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化遺產保護與民族發展研究的關係——以吐魯番地區為例」的核心成員,她曾三次赴新疆開展實地調研工作。這個與西域考古本毫無交集的南方姑娘,逐步掌握了拼接文化遺產碎片的鑰匙。
在吐魯番,徐婉玲頂着烈日,一遍又一遍地踏勘高昌故城,將殘破的城牆遺跡與歷史影像重疊。在高昌故城,她住在農家裡,從人類學研究視角,梳理勾勒出當地一家三代人職業變化與吐魯番地區發展的關聯。「在那裡,我們感受過火焰山的炎炎熱風,也看到了靜默遺址之上的燦爛星河。」從那一刻起,這個繡娘的女兒,決心拿起學術的「銀針」嘗試縫合文明的斷層。
「入宮」做學問
如果說徐婉玲的學術啟蒙發生在高昌故城,那麼,她的學術覺醒是在故宮文物南遷史料裡被點亮。
研究生畢業後,徐婉玲本想紮根吐魯番考古學術研究,奈何作為女性,西域研究常駐邊疆,較難顧及家庭。年滿30歲的時候,她決定再次改變人生方向。
上天總是眷顧努力的人。2008年9月,徐婉玲如願考入中國藝術研究院,並師從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先生。10月10日那天,是故宮博物院的院慶日,她接過導師贈予的學術專著《天府永藏:兩岸故宮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這是她博士生入學以來與導師的正式見面,既興奮又不安。曾經連繁體豎排信劄都讀不順的她,意識到自己站在了另一條史學研究的路上。
機會永遠留給有準備的人。2008年底,此時的徐婉玲已經入學三個月,對於自己未來論文的選題方向,心裡一直沒底。因為協助開題答辯會務的機會,她從師兄那裡得來一篇英文論文。師兄的本意是讓她試着翻譯,希望有助於她的學業研究,而這篇名為《故宮之為文化的再現》的文章,打開了她的學術視野。翻譯的過程中,她發現,台灣學者從他們獨特的視角來解讀兩岸故宮,帶給她極大的觸動。
從那時起,徐婉玲深刻地意識到故宮博物院在兩岸文化認同和歷史記憶方面產生的影響是如此深遠。借着到故宮博物院聽講座的機會,她把這篇翻譯文章交給導師。她不知道的是,講座後的第二天,鄭欣淼先生率團訪問台北,開啟了兩岸故宮博物院院長首次正式互訪。待鄭先生返京再見面後,兩岸故宮博物院的共同歷史研究,成了徐婉玲博士論文的選題。
隨着對史料的不斷深挖,紫禁城是如何從一座皇宮變成博物院?「一宮兩院」(一宮指一個故宮,兩院包括北京和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格局又是如何形成的?徐婉玲對故宮博物院早期的歷史產生濃厚的興趣,並慢慢地把目光集中在故宮文物南遷的歷史上。
抗日戰爭時期,為避免文物遭受劫掠或損毀,13000餘箱故宮文物遷移至上海、南京保存,後來又輾轉於湖南、湖北、廣西、貴州、陝西、四川。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文物損失慘重,唯故宮文物損失甚微。在戰爭歲月,社會各界人士為守護中華文化的根脈,留下了許多感人的真實故事和珍貴的歷史記憶。抗戰勝利後,這些文物又經歷了集中重慶、東歸南京、遷台和北返。從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2972箱故宮文物分三批運往台灣。自1950年1月至1958年9月,6253箱文物分三次運回北京故宮。
圍繞這場文物南遷,徐婉玲的博士論文逐步展開,之後「入宮」做學問,她也延續着這一研究方向,並逐漸成為故宮學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
藏在故宮文物南遷史裡的「密碼」
2010年6月,貴州省安順華嚴洞的鐘乳石滴着水。站在抗戰期間故宮文物南遷極為重要的一站,徐婉玲和來自兩岸故宮的學者一起,在潮濕的華嚴洞裡,辨識洞壁上的馬衡題記,丈量洞口處的面積,想像着當年文物箱件的安放位置。「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不僅讓我走進了歷史的現場,也因此與前來大陸考察的莊靈先生(老故宮人莊尚嚴先生之子)結下深厚的情誼。至今,我們依然保持密切聯繫。」
今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4月3日,台北故宮博物院前院長馮明珠率台灣寶吉祥文史教育協會一行近40名師生,與北京市第八中學師生共同參觀北京故宮博物院。踏入午門一路前行,馮明珠回憶起2009年的情景,「當時我們也是從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開始參觀。」彼時兩岸故宮博物院院長首次互訪,馮明珠陪同時任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赴京,兩岸故宮就文物展覽、圖書出版品、人員互訪與學習等達成多項共識。
徐婉玲說,兩岸故宮藏品之間的內在聯繫,是藏在故宮文物南遷史裡的「密碼」,是兩岸文化同根同源最為生動的表達。從故宮博物院1925年成立到1949年故宮部分文物遷台,兩岸故宮擁有共同記憶。其中,故宮文物南遷作為重要的歷史事件,至今仍持續影響着兩岸的人文格局。
「故宮文物可以具象地印證兩岸的文化連接。」以《九州如意圖》與《百福繁生圖》為例,它們都是乾隆時期詞臣汪承霈所繪。兩幅畫的構圖取勢如書法中的「龍門對」,形成空間與器物的完整敘事。抗戰時期,《九州如意圖》留平保管(北京舊稱北平),《百福繁生圖》南遷保存。現如今,前者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後者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兩幅畫作,分存兩地,卻記錄着中華文化藝術的基本脈絡,這是故宮文物互補性在兩岸館藏中的具體例證之一。
徐婉玲說,「兩岸在學術交流中,不存在史料多少的對比或珍貴程度的較量,我們本來就在一個體系裡。和,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太和,是和的至高境界。在文化的根脈上,兩岸就是一個整體,這是不可磨滅的。」